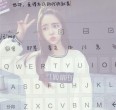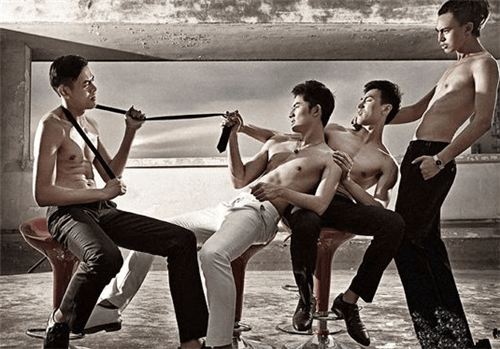
乌鸦兄弟搭窝续写作文【一】
森林里有一颗老树,树上有一个乌鸦窝,窝里住着一对乌鸦兄弟。
一天早晨,哥哥发现窝破了一个像小拇指一样的小洞。哥哥不紧不慢的说:“这么小的洞不用管,反正也不影响我们生活。”然后便扭过头去找吃的去了。
乌鸦弟弟也看到了那个洞,它说:“这个小洞我才懒得修呢。”说完便拍拍翅膀飞走了。
夏天到了,洞已经变得像李子那么大了。哥哥一边吃着冰棍一边悠闲地说:“弟弟,那个洞变大了,咱们要不要修修呀?”
“不用不用,我就不信它能再变大。”弟弟躺在树上懒懒地说。
夏天很快过去了,秋天来了,瑟瑟的秋吹进了像橙子一样大的洞,吹的兄弟俩直发抖,哥哥想:哼!我看你明天修不修窝。弟弟偷偷的想:反正还有哥哥呢,让他修去吧!
寒冷的冬天到了,哥哥和弟弟把被子裹的紧紧的,但也经不起风雪的打击,它们被冻了。
这则故事体现了一个道理,出现问题要及时解决,否则就会酿成大错。
乌鸦兄弟搭窝续写作文【二】
读《兄弟》的感觉犹如观看一幕舞台剧,《上部》(关于文革)是悲剧,《下部》(改革开放到现在)是喜剧;《上部》是悲剧中有喜剧,《下部》是喜剧中有悲剧;极度夸张的表演,极度粗鲁滑稽的语言,使得悲喜剧看起来都更似闹剧;舞台上的喧哗与动,让人对故事本身压根不想去信,而待沉静下来,对故事背后的现实却又不由不深信。
《兄弟》发表后,畅销的同时也遭遇了国内批评界无情的批评,国外的一些评论大概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兄弟》自始至终都非常有趣。中国的批评家们不满于余华故事的荒诞和形式的粗糙,他们更愤怒的是余华对当代中国生活坚持不懈的批评。《兄弟》……充满了对整个社会辛辣与深刻的嘲讽(美国《洛杉矶时报》20xx年2月1日);余华笔下的中国动不安,沉重压抑,畸形发展(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对这个世界余华根本不存希望(法国《读书》杂志)。
《兄弟》中描述的两个时代,用余华自己的话来概括,一个是“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命运惨淡的时代(文革)”,另一个是“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现在)”,从《兄弟<后记>》不难看出,余华在写作中国的遭遇时品味着欧洲的历史,而我在这本书中读到文革时不由自主想到了不久前英国的暴*,想到了利比亚总统卡扎菲之。英国暴*中参与打砸*的不少是学生,最小的不过10岁;卡扎菲被年轻的士兵抓到,士兵残暴地用鞋底抽打他的脸,虐打羞辱之后用枪结束了他的生命。卡扎菲曾问士兵:以我的年龄可以做你们的父亲了,我对你们做了什么你们要这样对待我?余华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特殊时代背景下人灵魂深处的恶和浊,只是,这恶和浊不仅仅属于中国。
有位诗人说: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余华坦言他与现实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说得严重一点,他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他写作的使命几乎就是发泄、控诉或揭露,他作品中充斥着暴力和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心的愤怒逐渐平息,他对事物有了理解之后的超然,开始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他的长篇小说一改过去的写作风格,尤其在《活着》、《许三观卖*记》里,他贴近小人物的生活,倾听他们心灵的声音,为他们的绝望悲悯叹息,又和他们一起在绝望中探寻活下去的希望,并为微渺的希望之光悲喜交集。
乌鸦兄弟搭窝续写作文【三】
五月一日,我和妈妈回老家过节,看望久别的爷爷奶奶。
老家的房子很大,房前屋后种满了各种蔬菜和农作物,有蚕豆、小麦、油菜……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象,空气也特别清新,我忍不住就在场上玩了起来。不知不觉,太阳下山了,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叽叽喳喳的声音,我循声望去,只见屋前的电线杆上停着两只燕子,它们你一言、我一语,似乎在商讨什么大事。过了一会儿,它们安静下来,一只燕子飞走了,另一只燕子叼来了草和泥,开始在屋檐下筑起巢来,想来它们刚才是在商量安家的地方呢!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后忙不迭去看燕子的窝搭得怎么样了。两只燕子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多半去寻找食物了,而它们的窝只搭了一点点。到了傍晚,它们回来了,又开始忙着搭窝。我真想帮它们一把,让它们早日把窝搭好,然后孵一窝可爱的燕子宝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