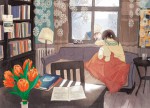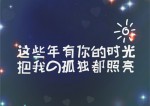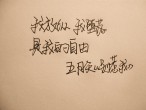用花来比喻人生的作文【一】
之所以说是一个失败的比喻,是因为作者似乎从头到尾都在有意将韩新月比作奥菲利亚,将楚雁潮比作哈姆雷特,就连最后郑晓京在新月之墓前都煞有介事地说了一句:“谁造出东西来比泥水匠、船匠或是木匠更坚固?掘墓的人!因为他造的房子可以一直住到世界末日。”本以为这一句有什么深意,没想到她淡淡地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你忘了吗?这是《哈姆雷特》里的台词。”(这部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缺点也是喜欢各种引经据典,导致文章十分冗长和啰嗦,这一点后面会说)如果说新月与奥菲利亚的共同点是她们都纯洁如白纸、善良近乎博爱,那么哈姆雷特的复仇对象是谁呢?难道要感叹一句“这是一个混乱颠倒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吗?显然不是。既然本无此意,那么就不该反复出现这个比喻。奥卡姆剃刀原理说的好:“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后来又仔细一想,假如按照这个比喻来的话,那么韩子奇难不成是克劳狄斯?这真的是细思恐极。
此外小说的辞藻过于复杂,本来没必要的`引经据典在这里频频出现,且对推动剧情发展没有任何作用,就比如上文提到的郑晓京在新月之墓前说的那句:“谁造出东西来比泥水匠、船匠或是木匠更坚固?掘墓的人!因为他造的房子可以一直住到世界末日。”紧接着又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你忘了吗?这是《哈姆雷特》里的台词。”和《月亮与六便士》里那句未说出口的圣经以及“一个先令就能买到十三只上等牡蛎的日子”相比这一段话的高下立见。《六便士》的结尾不仅读来让人心潮澎湃,而且回味悠长。还是那句话,“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那么为什么还要拿出来提一下呢?徒增文字而已了。
有点像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反复向读者强调:我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读过这些东西!虽然与主角的爱恨情仇没有什么必然关系但是就很想向你们科普一下!这个特点最明显的在新月的葬礼,本来非常悲伤的情绪都已经给渲染上来了,生生被那个繁复的葬礼仪式给冷下去了,不知道作者究竟想渲染个怎样的氛围,神圣吗?那就只需要把那些诵唱的经文用简单易懂的文字描述出来,或是于无声处彰显力量,而不是用那些看起来非常蹩脚的阿拉伯文的音译大费周章地给读者介绍葬礼流程。其实很多处介绍穆斯林传统的描写都有这个弊病,所谓气氛破坏者,说的就是这个了。读者可以百度的东西,就不要和百度一样写得那么程式化,(不过为作者辩解一下,她创作的那个年代还没有百度)至少要贴合剧情,否则就好像一块贴纸,随便找了一块墙贴上去,尽管很好看,却与雪白的墙面相比十分突兀。你要想藏一朵花,就应该把它藏在花丛中,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用花来比喻人生的作文【二】
一直觉得民国是一个很有气质的年代。应是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的传奇性值得被大写加粗地关注,值得被从头到脚地打望,把它在历史里单独成章,就是怕辱没了它的风韵。不谈时局如何如何动荡,只谈民国的文学是如何如何的儒雅而绮丽。张爱玲、杨绛、钱钟书、林徽因、徐志摩、萧红等一众文人墨客,构成了民国文学的绮丽,抑或者是儒雅。
比起民国的文学,我更喜欢民国的人,说话文绉绉的,办事也文绉绉的,可在面对爱情,却总嫌自己词不达意,恨自己眼神不够火热。从前看过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只记得他写张爱玲——“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看她的文字,只觉得她什么都晓得,其实她经历的世事很少,但这个时代的一切自会与她来交涉,好像花来衫里,影落池上”。我喜欢张爱玲,不因她华丽的笔调,也不因她在那个时代里特立独行的独特气韵,我只是很喜欢,她的文字带给我的感觉,她用扁平纸张上的白纸黑字,凭空让我看见了一个丰富的民国,是封建的,是遗憾的,是繁华的',更是一个爱而不得的时代,华丽而又苍凉。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民国于我的遇见,就好像是“花来衫里,影落池上”。多买了两本张爱玲的书,越看越喜欢,忍不住翻了一遍又一遍。她的文字是媒介,生生地把上个世纪香港、上海的繁华与落寞搬到了我面前。那些早已去的画面、化为黑白的情感与经历瞬间变得格外鲜艳,纷纷复活一样,从光阴的缝隙里漫溢出来。那些几十年前故事里的人儿早已消亡的笑,淌完的泪珠,倒是让我这个几十年后的局外人又笑了一笑,心生欢喜;又淌了眼泪,心口又绞痛了一番。书页间汩汩流动的,是民国的液与情感。
特别喜欢胡兰成笔下的张爱玲:“爱玲喜在房门外窥我坐在房中,她写道‘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沙金粉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琳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我当时就想,能有这般情怀,信手便写下这样一段话的人,怕是早就把所有人都甩在了她的橹声后面,以标准的凡夫俗子的姿态张望并艳羡她。
我一直庆幸的是,在我这个年纪,读过张爱玲的书和她的人。
喜不自胜。
我记得我曾经认识的第一个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是葛薇龙。《沉香屑?第一炉香》不算长,却让葛薇龙的形象有有肉,富有个性,却又轻易变得世俗。小说里的葛薇龙,是深渊里挣扎的一尾鱼,头尾疯了一样地摆动,奋力挣脱命运的桎梏,却抵不住命运的洪流。我们是蝼蚁,轻易无法撼动时代。多少具青春,在民国里长眠,又有多少只棺椁,经民国文人之手,多少年后又重新被敲开。爱玲写的是葛薇龙一个人,却平静且锋利地,写出了民国女性的奴性意识和女权的尚且卑微。那些故事里的香碎屑,在岁月的长河里洒落,成为生命里忽明忽暗的细灯,在扉黄的纸页上勾勒出一点扭曲的影。
民国。长衫遮了岁月,女子鬓角的卷发乱了经年。
我曾与民国有过一面之缘。
我见过它的。
用花来比喻人生的作文【三】
原文:
姓朱者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庄子《庄子·列御寇》
译文:
有一个姓朱的人,一心要学会一种别人都没有的技术,于是,就到支离益那里去学习宰龙的本领。他花尽了家里资产,用了整整三年时间,终于把宰龙的技术学到手了。
姓朱的得意洋洋地回到家里。可是,世间哪有龙可呢?结果,他学的技术一点也用不上。
寓意:学习必须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如果脱离了实际,再大的本领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