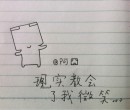红楼梦女性人物议论作文【一】
??盾与节本《红楼梦》议论文在很多时候,特别是在文学高手的笔下,“琐屑的故事”往往就充注着写实精神与社会意义,前者是后者的载体,删掉了前者,后者也就不复存在,茅盾与节本《红楼梦》。
茅盾先生并非专门的红学家,但在红学发展的历史上,他却做了一件连专门的红学家都不曾考虑和尝试,因而很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事情,这就是:亲自动手对《红楼梦》进行删削和压缩,从而完成了节本《红楼梦》的叙订。
茅盾叙订节本《红楼梦》是在1934年的春天。当时他居于上海,正与鲁迅、瞿秋白等一起,聚集于“左联”的旗帜下,积极从事多种形式的文学活动。而他自己的笔墨生涯也处在一个新的高潮之中: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整体场景为表现对象的系列小说次第展开,继长篇《子夜》之后,又发表了《春蚕》《秋收》《残冬》《林家铺子》等一系列短篇作品,以及大量的散文、杂文、随笔和速写;文学编辑和文学批评事业硕果不断,著名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选编完成并出版,广有影响的“作家论”等理论评论文章频频问世。在如此繁忙的情况下,茅盾为什么还要挤出时间和精力,从事节本《红楼梦》的叙订?已知的直接缘由是因为开明书店老板张锡琛,向茅盾提出了这方面的邀约,而张与茅盾都是浙籍文人,一向多有交情,故茅盾无法拒绝。至于张锡琛之所以选中茅盾承担节本《红楼梦》的叙订,除了因为茅盾是著名作家和学者,具有非凡的艺术鉴赏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他深知茅盾极为熟悉《红楼梦》。据钱君匀回忆,1926年的一天,张锡琛曾亲口对他和郑振铎讲过茅盾能够背诵《红楼梦》的事情。当时,郑振铎表示不信,为此,张与郑以酒席相赌。他们在开明书店专搞了一次酒叙,请茅盾、徐调孚、钱君匐、夏丐尊、周予同等人参加,趁着酒兴,由郑振铎点《红楼梦》的回目,茅盾背诵,结果茅盾竞滔滔不绝,大致不错地背了出来,以致让在场的众人十分惊讶,当然也由衷钦佩。(见《书衣集》)
当年的开明书店以出版青少年读物著称。该书店于1932年推出的由叶圣陶撰文、丰子恺插图,供初等小学用的国语课本,曾受到教育界人士的普遍赞誉,且影响广泛,迄今仍在吸引读者和出版家,前些时,还被多家主流媒体高调宣传和推荐。张锡琛诚邀茅盾叙订节本《红楼梦》,或许就是参照“国语读本”名家担纲为学子的与思路,所作的进一步的实验和拓展,其主要目的无疑在于向青少年普及文学经典和文学写作技巧,社会文化论文《茅盾与节本《红楼梦》》。关于这点,茅盾《节本红楼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自有交代。该文写道:“研究《红楼梦》的人很可以去读原书,但是中学生诸君倘使想从《红楼梦》学一点文学的技巧,则此部节本虽然未能尽善,或许还有点用处。”
不过,张锡琛毕竟是书店老板,他积极策划出版节本《红楼梦》,似乎也不是全无商业考虑。史料证明,1930年代中期的上海出版界,销路尚好的图书主要有两类:一是教科书及辅助读物;二是标点翻印的古籍,刘大杰选编的《明人小品集》,施蛰存选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以及出版史上反响较大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大都出现于这一时段。而节本《红楼梦》正好横跨这两类图书,或者说恰是这两类图书的交织物,它应当承载了出版者的市场期待和销售苦心。大约正是出于扩大发行的目的,《节本红楼梦》正式出版时,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瑕疵或破绽:书名所使用的意在区别于原本《红楼梦》的标识性前缀,不是两度出现于茅盾《导言》的`名副其实的“节本”,而是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洁本”。出版者做如此修饰,大约是为了告知市场:“这一部”《红楼梦》虽然描写了爱情,但文字是干净的,并没有“少年不宜”的内容,完全适合中学生阅读。殊不知熟悉中国古典小说的内行人都知道,《红楼梦》不是《金瓶梅》,它的文字清新典雅,凝练规范、诗性盎然,原本就不需要做什么清洁工作。这样一来,所谓“洁本”不仅显得无的放矢,弄巧成拙,而且变成了画蛇添足乃至故弄玄虚。
现在,我们具体来看茅盾是怎样叙订节本《红楼梦》的。还是在那篇《导言》中,茅盾很随意地写道:
陈独秀先生曾说:“我尝以为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见亚东版《红楼梦》陈序)在下何敢僭称“名手”,但对于陈先生这个提议,却感到兴味,不免大着胆子,唐突那《红楼梦》一遭儿。
乍一看来,这段话仿佛告诉人们,在如何叙订节本《红楼梦》的问题上,茅盾不仅受到陈独秀观点的启发,而且同意陈独秀提出的删节原则,即“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那么,哪些才是《红楼梦》中的“琐屑故事”?茅盾未作进一步诠释,我们还是来看陈独秀当年的原话。
1921年4月,时在广州执掌教政的陈独秀,应亚东图书馆汪原放之邀,为初版《红楼梦》写了一篇序言:《红楼梦(我以为用《石头记》好些)新叙》。在这篇不长的文章里,陈独秀首先对中国和西方小说进行了一番比较,认为:古代的中国和西方小说同样善述故事,那时小说和历史没有区别,中国和西方的小说也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近代以来,西方小说受实证科学的影响,发展了善写人情的一面,同时将善述故事的一面交给了历史;而中国小说虽然也发展了善写人情的一面,但却仍然承担着传布历史的责任,结果是“以小说而兼任历史的作用,一方面减少小说底趣味,一方面又减少历史底正确性”。因此,陈独秀明言:“我们一方面希望有许多留心社会状况的纯粹历史家出来,专任历史底工作;一方面希望有许多留心社会心理的纯粹小说家出来,专任小说底工作;分工进行,才是学术界底好现象。”接下来,陈独秀指出:
拿这个理论来看《石头记》,便可以看出作者善述故事和善写人情两种本领都有;但是他那种善述故事的本领,不但不能得到读者人人之欢迎,并且还有人觉得琐屑可厌;因为我们到底是把他当作小说读的人多,把他当作史料研究的人少。
《石头记》虽然有许多琐屑可厌的地更多内容请访问:中国 《茅盾与节本《红楼梦》》
红楼梦女性人物议论作文【二】
??红楼梦》的伟大有多少泡沫议论文在中国,恐怕连目不识丁的文盲,也能一知半解地听闻《红楼梦》是本奇书。至于稍识三两个字的国民,自然更会知晓《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古典名著,并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重要地位。再读点书,没人不知道在本国古往今来的作家之中排名论序,曹雪芹先生倘若是亚军,那么冠军位置铁定空缺无人。换言之,《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犹如泰斗,凭你学者专家,抑或百姓平民,若有只言片语的只弹不赞,便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亵渎,那些红学家们的痛心疾首状恐怕立时三刻就能令你无地自容。
《红楼梦》究竟有多伟大?有例为证,譬如人家托翁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巨著甚多,流传其广,尤其是《战争与和平》,连诸多文学大师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一干人等皆推崇备至,万千读者更是顶礼膜拜,怎不见出来个“托学会”抑或是“战学会”?偏偏本国之中,一部残缺之作竟有数百年的研究,其评点、评论、题咏、索隐、考证的范围之广,人员之众,绝对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单是这一条,可见它的伟大之处莫说当世谁可比肩,就是后世也可断言无人望其项背。
《红楼梦》的伟大之处林林总总,难以一言以蔽之,其中之一便是开篇即埋下草蛇灰线,暗示了最终诸人的结局。从主角到配角,无一遗漏,可见曹公心思之细密,的确令人叹为观止。然则流传后世的版本中,痛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部分。作为文学作品而言,凭你有多优秀伟大,也该遵循“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原则,然一部数百年前的残缺之作却被奉若神明,冠绝天下,甚至到了“连一个标点符号也改动不得”的.地步,其伟大程度难免有若干泡沫之嫌。
一部作品最最重要的便是大结局,盖因或有作者开头尚能字字珠玑,句句锦绣,写到后来不免才思枯竭,虎头蛇尾,当不起一部好作品之说;或有作者开头言语钝涩,写到后来反倒愈来愈流畅通达,不失为一部传世佳作。是否功亏一篑或者扭转乾坤全在结局的安排和功力,失去结局,犹似一个正常的健康人失去了下半身,完全不能行走站立,纵然有十分伟大,此时也去了三分。你几时见过一个残疾运动员再优秀,再能创造奇迹,因而成绩便能超过一个同样优秀的健康运动员?此乃客观事实决定,并非人力所能改变。
红迷常振振有辞,《红楼梦》缺失又如何?维纳斯断臂,残缺之美可不是依旧闻名天下,无人能及?此语实是大谬不然。维纳斯是一件活生生的艺术品,眉目分明,形象具体,美丑妍媸令人一目了然。《红楼梦》却完全不同此类,其抽象性注定了“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它的缺失之憾与维纳斯的残缺之美绝无可比性。故而,以此强辩,徒增笑柄。
《红楼梦》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文学史上分量颇重。独此一句,便可见泡沫。且不谈中西文化的差异,单是谐音人名这一节,洋人就不知所云,何谈理解,欣赏乃至推崇?曹公固然是功力已臻化境的语言大师,他又岂能一应周全到举世上下人人能读?莫说洋人,就是本国之内的同胞,若属少数民族不谙汉语,恐怕也是如对天书。换言之,一部不能在全世界普及的名著岂能妄称“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诚然,曹公将汉文学博大精深和美妙绝伦的魅力发挥到极至,可惜只能由汉语读者孤芳自赏,《红楼梦》虽伟大,局限性也可见一斑。与其鼓吹这部连完整译本尚空缺的奇书乃世界名著,不如放下妄自尊大的心态,潜移默化宣扬汉文化,直至洋人都十之八九成为汉语通,谁还敢质疑《红楼梦》并非世界名著?
《红楼梦》的伟大也在于曹公的创造力独步天下,这一点迄今无人敢比。此话当真有过满之嫌。李太白一代诗仙,尚因珠玉在前,不敢题诗,然后效仿崔氏作出“凤凰台上凤凰游”的名句。曹公的功力尚未达仙境,哪里就能才思泉涌到面面俱到的程度?譬如黛玉葬花,甄士隐顿悟后的“什么好什么了”的好了歌,在全书中虽属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然细究之后,原来这些是人家冯梦龙三言里早已用过的桥段。其余细节不胜枚举。曹公借鉴引用他人的创意原也无可厚非,只是一味撇清,堆砌盛赞他的伟大,泡沫不免又多了几分。
本国风俗,习惯造神。N年前,国际歌里分明写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们却偏偏大唱“人民的大救星”。造神的结果是举国上下走火入魔,大伤元气若干年。将《红楼梦》的伟大渲染到登峰造极,一览山小无异于造神,其结果同样有人重蹈覆辙。譬如刘心武先生。昔日的“刘心武”三字是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他的作品甚至被翻译成十种以上的文字出版发表。如今刘先生沉迷于红学研究,迹近走火入魔。先是丢掉自己的金字招牌,然后时不时语不惊人不休地俨然以红学家自居高谈阔论,虽屡遭正宗专家的驳斥,却依然孜孜不倦。本国就此少了一个优秀的一流作家,却多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三流红学家,也不知是《红楼梦》的伟大遗留出的泡沫,还是泡沫堆砌出了伟大。
还原历史真相,研究科学真理,为了这两样一味使出钩深索隐的态度,倒也算是严谨可爱。然一部文学作品,再多的假语存,再多的真事隐,终逃不了虚构的环节。用钻牛角尖的较真精神去研究这点虚构,自然是无穷无尽没完没了,继而派别丛生,你方唱罢我登场,接着各执一词,研究成果滚滚来。譬如起初是研究作品本身,结论可得出“连一个标点也改动不得”,再开始研究曹雪芹本人,莫说曹氏的六亲九族,只怕连与曹家沾边的阿猫阿狗也有来龙去脉。如此研究,最终既不能在官方的史书上添记一笔,也不能出来个某某原理造福后代,只不过在《红楼梦》的伟大上堆砌一层又一层的泡沫,留给国人闭门欣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