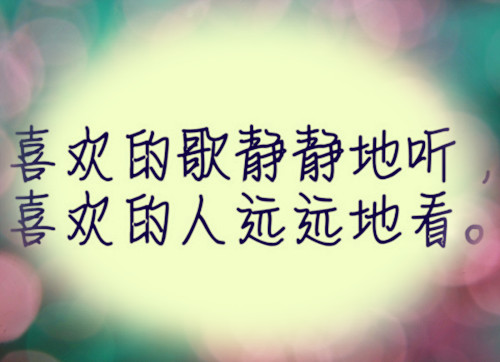
依稀记得那一面作文【一】
以前的我是个畏缩不前、毫无主见的小孩子,惧怕陌生人,惧怕任务,所以,那时的我什么都得依靠大人,衣食住行,都是依靠家长忙里忙外。
一天,外婆吃完酒宴回来带了一包糖,说这包是给舅妈的,妈妈想着外婆腿脚不好,自己要给外婆做晚饭,就想让我们小孩去。“你们哪个可以送糖去大舅家?”我的弟弟、妹妹、姐姐、侄子什么的,就一个劲地喊自己去。我家亲戚不知道哪来这么多,奶奶家的外婆家的,加起来起码有几十来个,什么大舅、舅妈,我连认都不认识,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于是我选择了沉默。可是妈妈注意到沉默不语的我,果断地把糖递给我说:“你去。”我的脸上写满了问号,手似乎动不了了,没有去接那盒糖。“我……”“舅妈家在后面山上的'那棵最高的树旁边,周围有一片玉米地。”妈妈淡定地对我说。“我不想去,我怕……”我胆怯地对妈妈说。妈妈皱皱眉头,说:“不行!就你去!有什么好怕的,你得改改你胆小的毛病,想让比你小的弟弟妹妹都喊你胆小鬼吗?”我这个人很爱面子,别人说我胆小我还真不情愿,于是结结巴巴地答应了。
我拿着糖出发了,按照妈妈说的路线走,要先走到一个岔口往右拐。我看着周围杂乱的树枝,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片树林的迷宫,无法走出去。路上黄泥可以盖过脚了,周围一些已经从树上折断交叉在一起的杂枝,犹如恶魔的瓜子在向我招手。我害怕极了,抱怨着:这糖非送不可吗?干嘛让我送?明知道我最怕来这种深山老林了!
走着走着,终于走到了岔路口,我果断地选择了向右走。谁知,路上突然蹿出来一条蛇,横卧在路上,虎视眈眈地瞪着我。我还要被蛇咬一口当买路钱吗?这叫我怎么走啊,我冷汗直冒,又不敢向前走。我心里又在一遍遍提醒着自己:不要慌,要镇定。我于是小心翼翼地迈开双脚,默念着:“放松啊,放轻松,不要怕,不看就好了。”我向前走去,没有看那条狰狞的让我冷汗直冒的蛇。不知是不是我的诚心打动了它,它竟像通了人性似的,慢慢地走开,让出了路。我又一步一步地小心地走过去,这才舒了口气。
我似乎不那么害怕了,加快了步伐,很快就上了平坦的大路。到了大舅家,他们亲切地招呼我,并给妈打电话说我已经送到了东西。告别大舅,我又一个人轻轻松松地下了山。
回来后,我似乎不那么胆小了。每次家里有任务,我会抢着接,也不怕是一个人了。妈妈也说,我变勇敢了,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胆小怕事的我了。
成长总需要锻炼,需要无数次出发,而那次出发,是我最难忘的。
依稀记得那一面作文【二】
“你作业写完了吗?”“你今天英语读了吗”“你名著看了没有?”脑海中是一串又一串各个老师苦口婆心的教导。“准备上补习班去了!”“你要不要学点特长!”“我建议你去上个游泳班!”父母的絮叨不停地在脑海中播放……是的,这就是我小学的日常生活:学习,疲倦,疲倦,学习……而即将步入初中生涯的我不禁为初中的生活所担忧:哎,肯定会更累,更忙!我晃晃脑袋,想要把心中所有的压力和沉闷甩掉!
是的,这学期结束后妈妈带着我开始了这次假期的旅行。我有幸来到了大草原。看着眼前广阔无垠的大草原,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一个字—爽!在春姑娘的滋养下所有的景象似乎都充满了活力与生机,小草郁郁葱葱,刚刚好没过我的脚踝。走在草地上,小草似乎抚摸着我的脚,顿时一股清凉直沁我的肺腑。脱了鞋,踩在上面,任由小草随意地在脚掌之间摩擦,小草似乎给我做一次免费的足底按摩,十分的舒适。“哇!这草原真美啊!天空真蓝,白云真美,鸟儿真自由!”站在小山坡上,望着远处那蓝水晶般的天空,天空中一朵朵白云在缓缓地飘动,几只鸟儿正在空中翱翔,看着天空如此的辽阔,白云如此的悠扬,鸟儿如此的悠哉,我不禁想要放声高歌:啊!大草原真自由啊,我好喜欢大草原啊,如果我也能这么轻松自由自在的生活就好了。我望着天空,大声呼喊着,想要释放掉心中所有的压力和沉闷!
“咦!那是小羊们吗?”带着疑问,我的目光集中到了河边成群结对的羊群身上,羊群们没有感受到我的存在,依旧悠闲自在的在碧绿的草坪上吃着鲜嫩的青草,乍一眼看过去,竟像是一块绿色的地毯上绣了许多雪白雪白的花儿。地毯上五彩缤纷的`野花更是给这绿色增添了许多色彩,在微风的吹拂下,花瓣在这天然的舞台上翩翩起舞,十分欢乐!“哇,真的是太美了,小羊们和谐地在吃着自己爱吃的食物,花瓣任意地在空中起舞,真是一副和谐美丽的图景啊!”不经意间,天一点一点地暗下来,很快,暮色就在这片大草原上落了下来。
夕阳西下,昏黄的阳光照射在这广阔的草原,草原好像换了件金黄色的夹克,这时羊羔们好像也害了羞,微微露出点儿粉色。而羊群们也都回到了羊圈,安静地睡下了。蝴蝶也跳累了,停在草丛中,慢慢地入睡了。坐在草原上我抬头看天,一轮明月高高地挂在空中,“真美啊!”,看着眼前安宁的一切,我早已将所有的烦恼与苦闷忘却了,只身沉浸在这份安静与平和当中。
“恩,该回去了,不然妈妈会担心了。”我一边嘀咕着一边站起来拍拍身上的衣服,迈着轻快的步履,走在回宾馆的路上,我感觉身体十分的轻巧,心胸更加宽广了,而心中的苦闷与压力也都慢慢释然了!确实,这一次出发让我受益匪浅:现代快节奏的生活让我们永远不愿意停下脚步,生怕比他人慢一步,于是我们便有了无数的压力与苦闷。然而偶尔地
驻足、停留,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只有这样,我们的视野才不必被遮蔽,我们的心胸我们才不会被限制,我们才能对生活中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依稀记得那一面作文【三】
故乡地处洞庭湖以北,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藕带、莲子、鸡头米,还有基围虾和长江鱼,仅是一想到,鼻腔里就尽是清新。父亲说以前家在东湖堤岸上,那是一个小小的湖泊。
出门就是烟波浩渺的湖水,与天相接。父亲说从小他就生活在江畔湖边,前面是湖,后面是长江,他是听着小船的桨声长大的。桨声悠悠,桨声清亮,桨声像一曲老腔,字正腔圆,唱出了水乡的苍凉和厚重。
小时候是和父亲一起划过船的,地点记不清了,只是那桨声在我耳畔,挥之不去。小船悠悠,我欢喜地将手伸到水面上,湖水轻轻地划过掌心,痒酥酥的。父亲边划着船,边笑道,小心别让那浪花咬破了手。我懵懂地问道,浪花有嘴吗?父亲笑道,有啊,这湖面就是浪花的一张大嘴啊!我记得,被湖水咬是很舒服的,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世上有一种咬,咬的叫人心花怒放。
父亲揶揄地说,别掉进湖里变成一条鱼,望着清澈的湖水,我想,要是真的'能变成一条鱼那该有多好。
我兴高采烈的坐在船头,父亲划着桨,桨板轻轻地滑过水面,潜入了碧水中,顿时桨声打破了清凌凌的湖水,打破了水乡静谧的湖泊,搅得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隐约记得后来回家,父亲是很失望的,他说那只是一个景区,并不是故乡的样子。而我不介意,沿海城市长大的我对于湖泊是很新鲜的,我的城市没有湖水。离开时我听见遥远的湖面上响起一阵此起彼伏的桨声,那桨声就像一首雄浑激昂的乐曲,在湖面上回荡,回荡在我的耳畔和心间。
夜晚在奶奶家,依旧是湖边的小菜,奶奶特意煮了鸭子,腌了鱼,还有鸡头米和银鱼莼菜羹,好像是有藕带的,那清香与湖畔的桨声一起,被我留在心里。
回家时我哭着吵着要把藕带和莲子带回广东,但仅一天车程就足以让藕带变老,莲子变苦。我只好将故乡变得小小地放进心里。后来我再也没有听到过湖畔的桨声,父亲也只是在饭桌上偶尔谈起长江鱼的滋味。对于故乡这个话题我们选择了缄默,我无权评论父亲的乡愁。
那天晚上我听见父亲用武汉话问母亲,暑假要不要带她去洞庭湖玩一玩?
母亲说那有什么好看的,无非就是划划船嘛。
我说不是的,那是我最难忘的桨声阵阵。
依稀记得那一面作文【四】
记忆中,大爷是个很忙碌的人,他似乎把每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甚至当我走在街上遇见他,他也在一刻不停的走着,走到我身旁时,他的脚步也没有停住,只是对我笑笑,然后什么话也没说的走了。那时候,我还不到大爷的肩膀,看他总是要抬起头来,可是当我抬起头,想渴望他叫我一声时,看到的却是一个笑脸。因为还小,所以对大爷印象就不怎么好,直到那天,他来我们家……
那天,我放学回到家,刚进门就大喊一声:“奶奶,我回来了!”结果拉上门,转过身就看见大爷的那笑脸,然后说:“怎么?不欢迎我啊?”“哦,原来是大爷。”虽然有两年没见,但大爷那笑脸还是印在了我的心里。大爷走上前抱起了我,说:“哈!两年没见,都长这么大了!”看到大爷今天这么闲,我不紧心里一震,皱起了眉头,想了一会儿,还是把藏在心里多年的'疑问问了出来:“大爷,为什么每次见到了,你都是那么匆忙呢?为什么见到我也不停下脚步呢?”大爷放下我,对我扯了一个笑脸,说:“老师没教过你们吗?一寸光阴不可轻啊!我这都快要入土的人了,更不能放弃活在世上的这点时间!”大爷说完,又给了我一个笑脸,我才发现,大爷老了,脸上已经有了那么多的皱纹。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送走了大爷。
没想到,那天,居然是我见到那笑脸的最后一天,一个星期后,大爷去世了。我默默地哭了。在梦里,我又看到了两年前,还没到大爷肩膀的我,走在街上抬起头,看到的那个没停住脚步叫我的人,看到了那张笑脸……
那笑脸,在我记忆里。
依稀记得那一面作文【五】
三、四岁之前的事情对于我从来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忆,我的故事,都只是奶奶与母亲闲聊时的往事,我曾很仔细的听着,用这些往事尝试着再一次编织起幼时的记忆。后来的变化,我都亲身经历,在我幼稚的脑中,牢牢地记住了我快乐时的许多物景。就像老屋被雨水冲刷参差而颤抖破裂的土墙,晚上睡下,便有老鼠在墙缝中欢跃奔跑,墙下枯藤老树,西风瘦马,母亲种下的豆角红色的小花,顺着院中的苹果树,一直攀上墙头。墙角古井辘轳,被岁月旋扭打磨得光滑圆润。墙侧的鸡巢中仍带着鸡腹温暖的蛋卵,被我的黑手一把抓住,欢呼奔跑着交给奶奶。我的身影,就在老屋的处处,我怀念着,就像记起当年的自己。
离开老屋时我只有三岁,随着父亲的奔波,要搬到河西戈壁一处劳改农场去,父亲为实现让我们一家辗转迁往城里的愿望,毅然背井离乡。奶奶不愿我离去,心里难过,时常在打理那么一点贫寒行囊的瞬间,眼泪便掉在破旧的包袱上。我们特意请来邻居的照相师傅,在我出生的床前,母亲抱着我,照了我的第二张相片,我歪着脑袋好奇的打量镜头,剃着小平头,眼睛漆黑明亮,穿着胸前还沾着一片没有洗掉泥污的绒线衣,胸口还绣着一只腾空的老鹰。母亲剪着齐耳的短发,微微笑着,脸上圆润而没有一丝皱纹。我的眼睛和母亲生得很像,同样透着天真淳朴的神光。她穿着自己亲手缝制的圆头领口,盘线纽扣的夹衣,黄底蓝线的格子,是那个时候的母亲。奶奶倚着门洞哭着,我一步都不曾离开过她,即便是去十里之外的外婆家,没有奶奶也是无论怎样也熬不到天亮的。我那样懵懂未知的远去,奶奶不知曾想念了多久,母亲不知是怎样难过忐忑的心情,摸索着一条漆黑不安的路程,再不见故乡的明月。
于是就到了戈壁滩中一个叫平川农场的地方。我的故乡并不是什么秀美的山川,依然山峦层叠,黄土丘陵,却精致而温暖,无论是泥泞的深巷小道,绊住了乡人的脚步,柴门后狂吠的黄狗,苍老的门洞槐树,檐下呢喃春燕,路中横卧的灰驴,或是荒凉的远山,山涧的铃响,田里等待一场春雨的麦禾,更有山前的溪流,水中嬉戏的顽童,我只到了这里,才觉故乡是那样美好平静。戈壁上没有山峦,一眼望去的尽是无限的沙尘和低矮的土丘,无趣的天空里偶尔飞过的大雁,枯竭的太阳和月亮,时而照着几分孤寂,时而隐在黄沙的后面,只如一副老画中隐约的一滴墨点,分明只是严酷和淡漠。唯一的树木便是屋前的白杨,几块初垦的菜田,用煤渣堆成的地垄,也能长出西瓜和西红柿。西瓜只能分得几个,沙地里的产物,真是甘甜滋润。西红柿却要冷落许多,成片的长着,熟透了就腐烂在地上,只是口渴时随手摘来,在衣襟上一擦便咬,汁水流出,也是爽口异常。最吸引人的,是常停在门口的一辆三轮摩托,白色的车身,碗口大的前照明灯透着几分神气,我央母亲扶着使劲爬上座椅,还够不着车把,便使劲的在装有弹簧的座椅上蹦搭几下。一旁还有一个专门乘坐的车斗,上面安装着一只替换的轮胎,仔细地研究一番,不肯下车,就这样拍了我最喜欢的这张相片。我歪斜地戴着一顶解放军黄绿土布的帽子,皱着眉头,毫无准备的面对着镜头,脸比离家时圆润了许多,个头明显的长高了,可仍有谁不放心我,从旁边伸出一只胳膊拽住了我的右手,我的不快,不知是相机快门的.一闪,还是因着那只胳膊。
这个荒芜又广阔的天地,连云彩都少有生出些许变化。每天跟着羊群,跑野了的伙伴,穿过一阵旋风,夹杂着母亲的呼喊。无趣时便去追逐一只慌张的野兔,看成群的麻雀乱哄哄地冲向枯燥的天空。戈壁滩分明而单调的四季,只有风是无论哪里都不曾遇到过的,刮起时,天昏地暗,连小块的砖头都会跟着跑起来。把脸贴在窗户上,听砂砾击打玻璃的声音。昏黄的灯下,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着衣物。母亲的手已然粗糙,却异常灵巧,就在白天时,还干着男人们才能干得动的体力活,一手牵我,一手用一根铁夹,捡拾卡车奔驰中跌落的煤渣。结伴的妇人爽朗而愉快地开着往事的玩笑,生活的风尘打在各自的脸上,紫红色的脸颊,顺手扯下头巾,只一擦,便随风而去。
我们在这里只匆匆地度过了一年,就传来了要撤离的消息。有人悄悄地在黄昏的灯下哭了,许多家庭依然挺立着,便如屋前那排孤独的白杨,有的家庭,却已在风中被吹得支离破散。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再一次收拾起简单的行装,各自奔往不同的前程。母亲照着父亲军装的样子赶制着我的一件新衣,鲜亮而俊俏的深绿色棱角分明,袖子和裤管做得很长,卷起来露在外面,又把父亲旧军装领口的红领章拆下来,缝在我的衣领上,我异常喜欢,背着父亲的水壶,同母亲在白杨树前照了张合影。母亲从故乡出来,依然还是当时的模样,只是那件圆口的夹衣,已然变成直角四方的狄卡式衣服了。
离去时的记忆,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我们这个小小的家,穿越苦难,搁浅在现在的小镇。父亲的愿望伴随着许多痛楚,终于艰难地实现了,但却不得不拿出更大的力量,重新建起我们的归巢。奶奶从故乡赶来,是怎样的情景,我都已经忘记了,我们这个家族的爱,从来都深埋在心里,只一瞬间,都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行动表达。唯有那件鲜绿的军装,我一直穿了许久。幼儿园时有次邻坐的顽童故意抹了污渍在这件衣服上,我不知是怎样的愤怒,使劲地咬了他的手指,老师惊异的看我,就像看一条饥饿的小狗守护自己的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