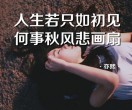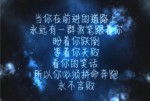写高中关于语文老师的作文【一】
我的语文老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她既没有鲜花那样的美丽,也没有那甜言蜜语,有的只是那几句通俗易懂的话语。也正是因为老师的这就几句口头禅,让我们每个学生都特别的尊敬她,时不时的便会提起,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记得我们刚刚入学的那时,小学的个性品质还依然存在(我们都来自于各个村小,再加中学科增多了,我们都不知道该怎样听课,各个犹如呆若木鸡。渐渐我们的听课的热情与日减少了,这是老师发现了我们的状况,便鼓励我们说:“不要害怕,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答错了没有关系的吗!”渐渐的我们胆大了,放纵自己了。课堂上偶尔也会听到窃窃的私语声了,大部分学生不知道记笔记,老师写在黑板上的重要的知识根本不知道从哪里记起,这时,老师就会用温和而又普通的话语说:“同学们,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呀!”学生都很听话的拿起自己的笔。
从那时起,我们的学习劲头都上来了,同学们也很喜欢她。课上的要求越来越严了,课上不许出一点的声音,我们似乎都很听话。但有些不太喜欢学习的学生,就坐不住了,课上竟然谈些与听课无关的话题。老师开始用目光暗示他们,他们看看老师后笑笑,接着该说还说,似乎是老师在和他们开玩笑。这时她边讲边往他们跟前走,用温和的语气说了句:“你别看我很温柔,只是没有人惹到我。”似乎有种让我们无法抗拒的力量。都乖乖的听老师讲课了。
从那时起,我们都开始学会听课了,但新的毛病也随之而来了。我们的语文老师用的是新的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主体,这篇课文设问题把课文的内容串起来,我们的思维都很敏捷,一个问题刚一出口,我们的答案就来了,七嘴八舌的各自都说自己的看法,哪还有老师说第二个问题呀,好长时间才可以说第二个问题,一节课下来仅能完成教学的一半。老师又总结了一句通俗易懂的语言。同学们听后都知道该怎样来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自那以后我们班的课堂纪律,听课状态,学习氛围都大有长进,我们的学习成绩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你知道那句话是什么吗?呵呵,是“叫话的鸟没有食吃”。
从此,这几句话就成了我们学习中时常提醒自己的“铭言”了。
其实,句句话中都寄托着老师的希望,虽说这几句话很简洁而又通俗,又那么真诚。但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刻在我们学生的心里。
写高中关于语文老师的作文【二】
当我第一次翻开《病隙碎笔》的时候,目光停留在了每一章节的前一页,那是史铁生先生创作这本书时的手稿,字迹清晰流畅。彼时我就坚信,这将是一份礼物,一份俯视着平凡人生的礼物。
周国平先生在解析书名的时候这样讲到:“体况恶化,写作又成奢望。大部分时间在受病折磨和与病搏斗,不折不扣是病隙碎笔,而且缝隙那样小得可怜!”不得不承认,对于史铁生本身,他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存在。在生命行走的路上,在那些像海绵一般的岁月里,他挤出了智慧,这种智慧,是从疾病的深渊中迸发出来的液。
《牧灵圣经》的扉页有这样一句话“我给你们一条新的诫命: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这是上帝对他的追随者的希冀,亦或者叫作命令。这是信仰的力量,如果上帝真的可以像他所诉说的那样爱着他的子民,那这世上又何谈灾难而言?
史铁生巧妙地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上帝不许诺光荣与福乐,但上帝保佑你的希望。”但可怕的是在这个满心功利的时代,我们的希望何在?当所有人拿着金钱和一颗所谓虔诚的心走进寺庙,向神明祈祷,而又有几个人祈祷的不是光荣而是希望呢?我们都坚定地认为希望就在自己的内心,甚至说走进庙堂就是体现了一种希望了的话。那信仰与名利的天平就已经倾斜地颓然不平了。
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个时代关于信仰的定义已经不再是它本该有的样子。史铁生用另一种方式,通过信心解读了关于信仰的理解:“信心,既然不需要事先的许诺,自然也就不必有事后的恭维,它的恩惠唯在渡涉苦难的时候可以领受。”与此同时,周国平先生却这样解读了这些文字:“任何一种信仰倘若不是以人的根本困境为出发点,它作为信仰的资格也是值得怀疑的。”
毫无疑问,我支持前者的观点,至少在现在看来史铁生用笔作足,已经用他自身的信仰行走过了他的人生。而这种信仰的开端,是没有以任何根本困境作为出发点的,就像他自己阐述的那样“不断地苦难才是不断地需要信心的原因。”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所以,在信仰的问题上,我们的根本观点应该是从什么时候看起,看了多远?
如果就困境而言,上帝无疑是公平的,诺贝尔用“生命,那是自然会给人类去雕琢的宝石。”这样一句话形容人生。我想,再也找不出任何文字能比这十六个字更恰当地解读生命了。自身对于自身而言,本来就是一种限制,一种突破不了的瓶颈。所以,上帝给了所有人根本的困境,只是每个人的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罗曼·罗兰说:“以来鄙薄自己,出卖自己,否定自己的。信仰,是世间最大的刑罚,最大的罪过。宁可受尽世间的痛苦和灾难,也千万不要走到这个地步。”他对信仰的作用做了高度的肯定,但问题在于当我们真正面对我们所信仰的东西时,却手足无措,甚至无法完整地表述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信仰还只是头脑中的一颗小芽,从未开花。
还是史铁生说得好:“路的没有尽头,便是他遥遥地总在前面,保持着希望永不枯竭。”这是前人恳切的话语,希望永远是和信仰并存的。如果没有希望而空有信仰,那无疑是一个空壳,或者说没有信仰而只有希望,那也仅仅是一种空想罢了。最可怕的是,这个我们熟稔的生命中,总有一些人既没有希望,也没有信仰,那“倘若一眠能了结心灵之苦楚与肉体之百患,那么,此结局是可盼的!”(莎士比亚《生与》)。对于信仰,料必大多数人抱着可望而不可即的心态,也正是由于这种误解,信仰渐渐成为了有思想的人的标签。墨西哥有部老电影叫做《美丽的秘密》,它提到:“如果失去自我,你的抗争结果注定是失败的。”毫无疑问,自我是每个人赖以生存的资本,当开始正视自我所存在的价值时,人生、感情、关爱,还有思考都不再是更高一层人生价值的体现了。
“只要你往前走,他总是给路。”行走和道路是同一种存在,但天堂与现实总是有着永恒的距离,如果对于每一个步伐都充满了胆怯,那就不仅仅是距离的问题了,那是没有了希望,心中就根本不存在天堂。“理智本身是一种信仰。它是一种确定自己思想和现实之间关系的信仰。”(切斯特顿语),就信仰最初的样子来讲,它是一种限制行动的行为准则,对于史铁生而言,它更是让他直立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中想走的双脚。
没有人能像史铁生那样勇敢,他的身体是残缺的,但思想却始终驰骋在无疆之域。这或许是对信仰最有有肉的诠释。“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笔去找。”(《我与地坛》),如当我发现他手中的笔就是他信仰的具象时,我不由得感到胆怯,能有多少人能把一种信仰表现的这样恰当得体,并与亡抗争呢?
再小的空隙,也是有光芒的。遗憾的是,没有几个人能向正确的方向走去。大家都太仓促了,从一开始就义无反顾地奔向了亡。让我们将时光退回到创作这本书的年代,那时史铁生的病情被确认转为尿毒症,终至三天透析一次。就是在这样的循环中,他写下了这种文字,因为他不惧怕亡,不惧怕痛苦,我想,整本书里的每个字都是有声音的。它们或深沉,把疾病带给他的痛苦用一种平和的方式娓娓道来;或淳朴,用常人无法理解的乐观向上,诉说着他强有力的人生领悟。